语
再以本文
揭 秘 王 维 诗
泰安长城中学 薛玉海
本文属于东施效颦,模仿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而作。
《红楼梦》第48回“呆头呆脑的”(宝钗语)香菱拜黛玉为师,初读王维诗“领略了些滋味”,讲了三联给黛玉听,分别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三联各出自王维《使至塞上》、《送邢桂州》、《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这节课不妨称之为《王维诗三首》。现在的高中语文课也常有《王维诗三首》的课文,(比如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选修本《唐宋诗词》,所选篇目基本上与《红楼梦》版相同,只不过换掉了《送邢桂州》),但是我们今天的编选和教学从量到质都与《红楼梦》版不可同日而语。首先,《红楼梦》中的《王维诗三首》是一百首中的三首,是“把他的五言律读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后,再来“讲究讨论”;其次,《红楼梦》中是学生在“领略了些滋味”后自己讲诗,

香菱学诗的劲头着实让人感动,我也尝试读了《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学着发了一回呆,“领略了些滋味,不知可是不是,说与你听听。”刘心武在“揭秘”时一再声明“我从来不觉得我自己的观点都是对的”,那么我仅仅是“学着顽罢了”,让你见笑了。


香菱说:诗的好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寒山转苍翠”,“寒山”恐怕不是“寒山寺”的寒山,山为什么寒,季节变冷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根据生活经验,有暮蝉的秋,还算不上深秋,只能说有凉意,说不上寒冷,因而说“寒山” 似乎是无理的。佛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无生”,“无生”是“寂灭”或“涅梁”的另一种表达式,是空无寂静的解脱境界,作者虽没有出家却一生奉佛,常用静、寂、疏、深、寒等词写诗营造这种空灵静穆境界,如果抛开这层含义,说“寒山”也是“有理有情”的。《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我以为山寒主要言其山高,海拔每升高千米,气温便下降6度。不直言山高,而用温度写高度,实在是妙。苍翠,青绿色,写山色,“转苍翠”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用颜色写季节,由夏季过渡到秋季,但是深山颜色的变化往往是不明显的,特别是长满苍松翠柏的大山,诗人能敏锐的把握这一细微变化,说明诗人居山林已久,(从下句的“日”也能反映出),极其喜爱山水,否则不会观察的这么仔细;二是用颜色的深浅、明暗的变化写一天当中时光的流逝,写出了夕阳西下的山色愈来愈深,愈来愈浓。用颜色写时间,反映出诗人构思的精巧,一个“转”字一举多得,也让静止的山动了起来,一幅寒山图有了诗的灵动性,姑且看作是“画中有诗”吧。
黛玉教导香菱断不可学“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这种浅近的诗,而极力推荐王维的诗,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王维的诗的确是极富哲理的,可以说王维是诗人哲学家,清代徐增在《而庵诗话》中曾指出“摩诘以理趣胜”。如果说“寒山转苍翠”体现了“静中有动”的话,“秋水日潺湲”则体现了“动中有静”。潺湲,水流声,溪水的潺湲本来是有的,但在秋风中给人的感觉却是似有似无,时有时无,一个“日”字又把这流水声给“凝固”了,象是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这就是所谓的“诗中有画”吧,这让我想起了李白的“遥看瀑布挂前川”,一幅是看到的,一幅是“听”到的,一幅水势大些,一幅声势小些。哲学上的静止有两种情形,一是指事物之间的空间位置保持不变,二是指事物某一方面的性质在一定时期内基本不变。“日潺湲”是后一种静止,甚至听久了就听不到“潺湲”了,就像入芝兰之室,久闻而不知其香。即使“潺湲”时时在耳,则更感觉寒山之静穆。
由于受到母亲的影响,王维从小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有着深厚缘分。佛教中的禅追求的是一种宁静淡泊的美,“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而动的存在更彰显了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王维《鸟鸣涧》)我国近代美学大家宗白华说过:“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照常,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中国的山水文人画、诗歌、园林,都将“禅”的这种空明恬淡的意境,这种不可言说的韵味融进了诗中、画中。人说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句字字入禅,从这两首诗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动静不二”是贯穿全诗的,静有寒山、柴门、渡头、墟里、五柳,有声的动有潺湲、暮蝉、狂歌,无声的动有转、临风、落、上等。当然除了动与静的哲理,我们还可以读到明暗、深浅、虚实、远近、高低、荣辱、利害、得失、进退以及落与上、天与人、人与物、醉与醒等等。
“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寒山”中的“暮蝉”也可以说成是“寒蝉”了。晋朝陆云《陆清河集·寒蝉赋》有“寒蝉哀鸣,其声也悲”的句子,宋朝柳永在《雨霖铃》中说“寒蝉凄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但是“倚杖” 听到的“暮蝉”并不悲哀和凄切,反而是感到生命的坚韧、顽强、可爱、可敬,让人觉得寒山虽然空寂但不失生气;他在“清秋节”也并不显“冷落”和悲伤,就像是画中人在倚杖临风,看寒山苍翠、渡头落日、墟里孤烟,听秋水潺湲、暮蝉阵阵、朋友狂歌,气定神闲,物我两忘,天人合一,令人羡慕。
“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 《红楼梦》第48回香菱对“余”字和 “上”字很感兴趣,正是所谓“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不过此前黛玉曾说道:“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这一联不仅有奇句,更有意趣,透过诗中美景我们可以感受到王维陶醉在喧嚣过后的宁静,欣赏着远离险恶仕途的农家生活的纯朴、自然、和谐。此时,如果诗人自己把“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加以比较,我想他可能更喜欢前者。《而庵说唐诗》说:“‘大漠’‘ 长河’一联,独绝千古。”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战争”,作为一首边塞诗,《使至塞上》几乎句句不离战争,给人一种草木皆兵、一触即发的紧张感和压抑感,这景色写的越美,越反衬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残酷。“使至塞上”,仅仅是战争悲剧的序幕!“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诚然战争也可以演绎游侠意气、慷慨悲壮、浪漫豪情,但是它的暴力和血腥味,无论如何也比不上辋川闲居的幽静和甜美,大漠孤烟无论怎样笔直,也赶不上墟烟依依的温柔,震天动地的战鼓声和喊杀声,就不如秋水潺湲、暮蝉阵鸣悦耳。此时,倚杖老者在静静的看,在静静的听,也许脑海中偶尔会闪过一些不平静的画面:使至塞上的颠簸(外患),安史之乱的被俘(内忧),平叛后侥幸躲过的杀头之祸(人生大难),官场的拥挤(仕途险恶)……这些画面闪过后,他更加专注了,仿佛化为山水的一部分,也许他已经醉了,要不是有杖倚着,很可能醉卧柴门前了,并且醉的很深,已不能“狂歌”了。
我对“孤”字也挺关注。“孤烟”是否意味着地处偏远,人烟稀少?我也常常疑惑:古人隐居是否是远离人间繁华、消极避世呢?细读这首诗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这样。这里有发达的航运,“渡头余落日”,一个“余”字反衬出白天渡头熙来攘往的繁忙;山腰有别墅,墟里有农舍,别墅有官宦,酒馆有醉客,柳前有秀才,孤烟有农妇,山上有隐士,渡头有游客(《新唐书·王维传》:“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泮、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 明月竹林,白石清滩,空山青苔,古木衰柳,飞鸟夕岚相伴,欹湖箫声飞扬,没准当时的旅游业也很发达。),好像这里士农工商均有,三教九流汇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旅游业各产业繁荣。这样看来,“孤烟”仅仅是墟里的第一缕炊烟而已!如果再看看王维绘制的《辋川图》,我们就更清楚“孤烟”不孤,甚至会怀疑“倚杖柴门”的真实性(如果把诗当说明文来读),因为别墅的院门和房门都不可能是“柴门”。 “柴门”是虚写,仅仅是一个符号而已,是代表隐士居所及田园生活的最典型的意象之一。由此可知古人归隐决不是回避、排斥物质文明,把人变成苦行僧。王维被后人称为“诗佛”,而“佛法在世间”,禅宗强调佛教的修行活动不能脱离世间,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要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对自身心中佛性的认知。

尾联写到了隐士的诗酒生活。又遇裴迪,倍感亲切,题诗相赠,照应了题目中“赠裴秀才迪”;接舆(比裴迪)与“五柳”(作者以陶潜自比)志同道合,“穿越”神交,题目之“辋川闲居”也就落到实处。王维写这首诗时还在朝廷做官,虽常在辋川别墅与友人弹琴赋诗,悠游岁月,但并未完全“隐居”,过的是“半官半隐”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辋川闲居”。 “半官半隐”, 亦官亦隐 ,被称为“朝隐”, 白居易《中隐》诗中说的 “大隐住朝市”就是这种情况。隐逸是中国古代文人一种传统心路选择和生活方式,而“朝隐”, 又是魏晋以后士大夫文人津津以求的生活途径。我们应该理解这种隐逸文化,因为腐败在专制体制内是无法解决的,隐逸就成了无数文人与污浊世俗抗争失败后的自然的心路选择,所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不能指责他们的逃避与消极,最起码在精神上他们从仕途的险恶与官场的腐败中退出来,不再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这就难能可贵。
初读尾联,我并不知“接舆”是谁,但读到“狂歌”时,我想到了鲁迅,觉得《狂人日记》有了“歌曲版”,看来“狂人”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尾联的“醉”是高人隐者追求的境界,乱世的大醉即是心灵的独醒;一个“复”字说明不是第一回醉了。不同的人醉态是不一样的,“接舆”醉后是狂歌,没有“伴君如伴虎”的惶恐,没有官场的虚与委蛇、口是心非、矫揉造作、谨小慎微,有的是人格的独立、个性的张扬与气节的坚守,自然纯真,自在洒脱,放荡不羁。就写景而言,颈联是千古名句,但就立意而言,我觉得尾联的地位极其重要。
如果单从读诗的感觉看,作为俗人,仅读前三联,我并不十分喜欢诗人用寒山、苍翠、秋水、倚杖、暮蝉、落日、孤烟塑造的禅境,因为它给人一种凄凉、沉寂、灰暗、衰老、孤独、悲伤之感,但是读了尾联后,仿佛眼前一亮,原先的感觉一扫而光,诗中隐士的冰清玉洁的节操,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全诗,诗中的景物顿时明快起来,一曲“狂歌”“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寒山透出些许暖意,苍翠更显无限生机;秋水更加清澈,潺湲更觉纯净;倚杖临风,飘逸睿智,暮蝉阵鸣,只争朝夕;夕阳落下,炊烟升起,倦鸟归巢,人叙天伦;朋友狂歌,知己赠诗,惺惺相惜,情真意切;风光人物,相映成趣,物我一体,情景交融。禅宗认为,众生皆有佛性,皆可成佛,诗人笔下,万物都有了佛性、灵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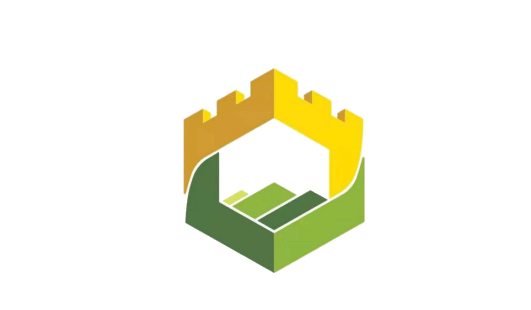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