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虽身在城市里,冷不丁地听到布谷鸟的啼鸣,我的眼前还是会立刻幻化出一幅农田麦收的画面:麦浪滚滚,热风吹拂,镰刀挥舞,汗洒如雨。。。。。。
我已离开农村许多年了,可这样的场面每每回想起来,我依然心有余悸。
我出生在农村,祖辈是农民,父母亲也都是农民,而且他们一辈子从未离开过农业生产,是地地道道的做了一辈子的农民(虽然现在他们跟随儿女来到了城市里安度晚年)。
由此我作为家中兄弟姊妹排行中的老大,自然“近水楼台”,从小也跟从父辈在田地上长大。
农村的孩子们自小就得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家活。我的农家活的历史要追溯到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那是70年代初,每到农忙季节学校都要放假,俗称麦假和秋假,麦假放两周,秋假放三周。放假后,我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麦假是去刚收割的麦地里捡麦穗,秋假是割草或到犁耙过的田地里砸坷垃。生产队会按各人表现和年龄大小给评工分,我那时每天可以记四分工,折合人民币价值八分钱。
后来上了初中,干的农活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再后来上了高中,每到假期甚至周末,都差不多是生产队里的整劳力了。
那时候农村最累的活莫过于割麦子,没有收割机,没有农具,有的只是一把镰刀,一眼望不到头的麦陇,一把一把的割,一点一点的前进,汗水吧嗒吧嗒地往下掉,口干舌燥,头晕眼花,腰酸背痛,那真的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呀。
还有一样农活,不是很累,但挺苦,就是秋季到即将收获的玉米地里“打玉米叶”,因为早上凉爽的时候有露水,所以这个农活都是中午做,一阵活下来,往往是手臂、脖子和面部都被玉米叶划伤了,一出汗,就火辣辣的疼。
1977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后,就算是整劳动力了,每天听队长的钟声上下工,这年我十六周岁,生产队里给我记十分工,约合两角钱。
这期间我做过饲养员,赶过牛车,参加过“战山河大会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学会了推装满约有四五百斤东西的独轮车。
那时的农家活不但累,而且一年到头的忙,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到现在有两件事情我还记得一清二楚,一件是因为晚上参加生产队里的积肥“夜战”,睡眠严重不足,吃早饭时竟然打起了盹,饭碗掉在了地上。另一次是除夕之夜被队长安排去“看水”浇麦地,挣了双倍的工分,也就是四角钱,当时为能够得到这样的“美差”而欣喜不已。
我在农村土生土长了17年,直到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才离开家乡。
可以说农村里所有的农活我都干过,割麦、打场、赶车、耕地、翻地、播种(从我的博客中可以看出我会时不时的有那么一两句的农民用语出现),更别说割草,捡麦穗这些小的农活了,甚至是凌晨天还未明就起床去捡粪之类的也干过,把捡了的粪肥卖给生产队里挣工分-------因为我的弟弟妹妹年龄小,家里人口多,如果工分挣不够,就要被扣掉“口粮”。
那时,我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农民,所有城市里的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甚至包括去公社、县城,去外婆家都是走路,没有自行车,全身上下也都是标准的农民装束。
1978年3月,托小平同志之福,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我进入了师范学校再次读书,原以为吃了笔杆饭,就要从此与土地说再见,那日晒雨淋的农民记忆将渐渐远去,直至消失,没想到1980年当了教师后,却时常还要重温农夫生活,甚至更加辛苦和劳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庄稼人被解放出来了,每年就干几个月的活就行了,不用再一年到头的忙活。
我父母也承包了土地(刚工作时,我的工资甚至不到三十元,这时候土地上的收入是我家生活的主要来源),虽然只有六七亩,但都是水浇地(良田),真正把它侍弄好,也要付出艰辛的劳作。我的父亲身体不好,多年的胃溃疡,一到农忙就疼得厉害,母亲也老早就患上了高血压,我的弟弟妹妹年龄小,而且还都在都在上学,我家承包的土地仅靠我的父母在农忙时根本照顾不过来,特别是我们村里那时已经开始种经济作物了,而经济作物需要投入的劳力更多。
所以我仍然要经常的到农田里去劳动。
这就是我的亦工亦农的生活,也可以说这时我是兼职农民。
这时候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我都是天不明就赶紧回到离工作单位十多里的自己家承包的农田里去劳作,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离开。后来和妻子结婚了,同样做教师的妻子心疼我,也和我一样成了兼职农民。
在做兼职农民的这段时间里,我和妻子掌握了一项技术含量很高的农活-------“扬场”,百度百科上是这样解释“扬场”的:“用木锨等农具播扬谷物、豆类等,以去掉壳、叶和尘土。”麦子脱粒后,我和妻子先在地上画一条直线,然后妻子用木锨将麦糠麦粒放到我端着的簸箕里,我迎风倾出,使得麦粒和麦糠在风的作用下脱离开来,这可是很多的老农民都不会的农活,我和妻子学会了。
还有一件事给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我家种了一种“三七系棉花”(可能叫这个名字),这种棉花纤维长,而且棉籽还可做种子,价格比较高。但种这种棉花最苦的活就是喷农药,而喷药效果最好的时间是正午,结果有一天我因未穿长袖服装,喷药时顺风将雾状农药吹拂在我的手臂上,以致产生了吸入性的农药中毒,我头晕呕吐、胸闷憋气,整整折腾了一夜,中毒症状才得以缓解,这次事件让我记住了这种毒性很强的农药:它的名字叫“呋喃丹”。
别以为我做了这么多的农活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我不但没有影响我的教学,而且还工作的很好:我那时候差不多连年担任毕业班班主任,我的班级是学校里考上人数最多的,我所教的学科平均分总是稳居学校统考的第一名,我所教的学生也曾连续三年在升学考试中摘取全县语文学科单科最高分的桂冠,我也因工作认真积极先后被提拔为教研组长、级部主任、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
这样的生活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因为工作需要离开家乡调动到泰城,在来泰城之前,我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父母承包的土地退还给了村里,因为这时我家已经不再仅仅依靠土地为生了,我的弟弟妹妹也都大学毕业陆续参加了工作。
从这时我才算是正式的脱离了农田,脱离了农民生活。
来到了泰城,单位宿舍楼的房前屋后有时候也有一些空地,邻居们稍有闲暇会去开垦一块,种点蔬菜,而我从不去种任何的东西------我实在不想再勾起我对我的农民生活的任何的回忆。
我是在泥土里长大的,我前前后后在土地上摸爬滚打近二十年,深知农村人的不易。
我读书时,尽管就在文革中,但我很用功,因为我害怕干农活,不是我懒惰,实在是我亲眼目睹知道农民太苦了--------那个时候,农活基本都是人力操作的,机器用得很少,就是偶尔有人用,还很贵,开销很大,靠人力来干农活的,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工作后,异常的卖力,不论是否评选我为先进。我参加工作至今三十多年了,工作中我从来未感到过所谓的苦和累,因为和农民相比,我的教师生活,简直太轻松了,真的是一种享受。
即便是每每遇到挫折,只要想到当年的农民经历,一股莫名的力量就会从心底而来,我会很快抚平心中的创伤,忘掉所受的所有委屈和不痛快,努力工作,执着前进-------再苦再难还能苦过难过当农民吗?
今天是端午节,也是农历节气的“芒种”,早晨还没有起床就听到了布谷鸟清脆的啼叫,农村正是麦收时节,尽管现在早已不用人工收割了,听到布谷鸟的啼叫声,我还是不由自主的回忆起了那大太阳底下挥汗如雨的镜头,我始终忘不掉。而且每每忆起,我总是心潮澎湃、此起彼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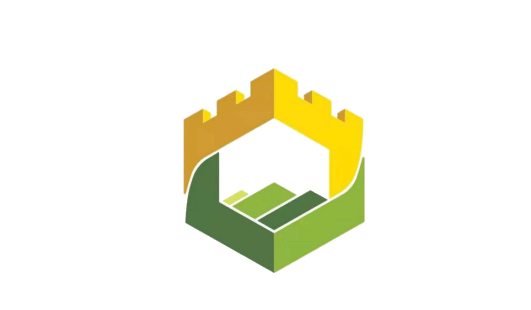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